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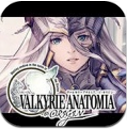

“五一六通知”的發起及其原因探析

1966年5月1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通過了著名的《中國我黨中央委員會通知》,即“五一六通知”。這一通知的發布標誌著中國進入了長達十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時期。那麼,“五一六通知”究竟是如何發起的?其背後的原因又是什麼?本文將從曆史背景、政治環境、思想鬥爭等多個維度進行探討。
1960年代初,中國我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內進行了一係列爭論。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,黨內開始反思蘇聯模式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影響,同時也在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。在這一背景下,中共中央於1964年7月專門成立了領導思想文化工作的機構——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,組長為彭真,成員包括陸定一、康生、周揚、吳冷西等。這一機構的成立,原本是為了加強對思想文化領域的領導,但在“左”傾思想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的形勢下,一係列學術、文藝觀點被扣上了修正主義等大帽子,並遭到公開批判。
1965年11月10日,上海《文彙報》發表《評新編曆史劇〈海瑞罷官〉》,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、曆史學家吳晗,稱《海瑞罷官》是為右傾機會主義翻案,“是一株毒草”。這一事件迅速成為思想文化領域鬥爭的焦點。在此背景下,文革五人小組於1966年2月製定了《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》,即《二月提綱》。《二月提綱》提出“要堅持實事求是,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,要以理服人,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”。其本意是約束文化領域的大批判,防止其進一步發展為政治鬥爭。
然而,《二月提綱》的出台並未平息思想文化領域的紛爭,反而引發了更為激烈的爭論。主席對《二月提綱》提出了尖銳批評,認為其混淆了階級界限,未能準確揭示出文化領域內的階級鬥爭。在此背景下,1966年4月,林彪、江青主持的《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》經主席審閱修改後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。《紀要》宣稱建國以來文藝界“被一條與主席思想相對立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”,要求“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,徹底搞掉這條黑線”。
隨著思想文化領域鬥爭的升級,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了擴大會議。會議由劉少奇主持,主席、周恩來、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均出席。會議期間,對彭真及《二月提綱》進行了嚴厲批判,並成立了“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”,成員包括陳伯達、康生、江青、張春橋等,負責起草《中國我黨中央委員會通知》。
5月16日,會議通過了由主席主持起草的《中國我黨中央委員會通知》,即“五一六通知”。《通知》宣布撤銷《二月提綱》和“文化革命五人小組”及其辦事機構,提出重新設立“文化革命小組”,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。這一決定是為了開展“文化大革命”而采取的組織措施。《通知》還羅列了《二月提綱》的所謂十大罪狀,逐條批判,並提出了一套“左”的理論、路線、方針、政策。
在結語部分,《通知》要求各級黨委立即停止執行《二月提綱》,奪取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,號召向黨、政、軍、文各界的“資產階級代表人物”猛烈開火。這些從“左”的觀點出發的要求和估計,嚴重脫離了實際,為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發動奠定了理論基礎。
“五一六通知”的發起,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。首先,從國際環境來看,中蘇關係的惡化使得中國我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內更加警惕所謂的“修正主義”傾向,試圖通過“文化大革命”來清除黨內的“資產階級代表人物”,鞏固無產階級專政。
其次,從國內政治環境來看,“左”傾思想在黨內逐漸占據主導地位。在主席看來,黨內存在著一股與主席思想相對立的“黑線”,必須通過“文化大革命”來徹底揭露和批判這條“黑線”。同時,主席也試圖通過這一運動來加強自己的領導地位,鞏固個人崇拜。
此外,從思想文化領域來看,《二月提綱》的出台未能平息思想文化領域的紛爭,反而引發了更為激烈的爭論。主席對《二月提綱》的批評以及隨後的一係列事件,使得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發動成為了必然趨勢。而“五一六通知”的發布,則是這一趨勢的具體體現。
“五一六通知”的發布,標誌著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正式發動。此後,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批判鬥爭。在這場運動中,無數無辜者受到迫害和摧殘,黨的組織和國家機構遭到嚴重破壞。同時,“文化大革命”也導致了中國經濟的停滯和倒退,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。
盡管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最終目的是清除黨內的“資產階級代表人物”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,但實踐證明這一運動嚴重偏離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。它給中國帶來的破壞和災難是深遠的,也是無法彌補的。
綜上所述,“五一六通知”的發起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。它既反映了當時國際環境的複雜性和國內政治環境的動蕩性,也揭示了“左”傾思想對中國我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嚴重危害。曆史的教訓是深刻的,我們應該銘記這段曆史,從中汲取教訓,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,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。